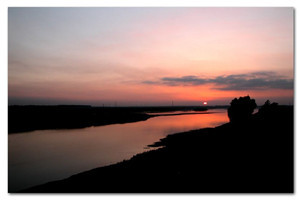婚异
河南修武县文化源远历史悠久,是个千年古县。自元明以来当地就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凡是家中有儿子的到了十三四岁就会给他早早完婚娶个媳妇,而通常儿媳要比儿子年长数岁,有的甚至会年长十岁以上,这样既能细心照顾夫君的衣食起居,也可以早早帮助公婆操持家务。到了康熙初年,当地的一家邹姓农户为自己刚满十三岁的儿子娶了房媳妇,这媳妇娘家姓刘,年方二十正是桃李年华,虽说也是邻村农家之女,却生得杏眼弯眉面容甜美,颇有几分姿色。邹家在村中虽不是大富却也是小康,家中还请有几个长工仆人,邹翁的爱子名叫天贵,尚是一个面容稚嫩的垂髫少年。
头天新人过门,自是敲锣打鼓笙歌鼎沸,宾朋高坐热闹非凡,直到晚上众人才慢慢散去,一对新人也早早入了洞房。不料待得第二天日头高照,邹家老俩口却不见小夫妻按俗礼给他们请安。邹翁心道: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可现在天已近午,就算儿子年幼贪睡,这儿媳刘氏总该起身问安了吧?莫不是有什么意外不成?想至此处二老便来到新房门前呼叫儿子的名字,叫了数声方听天贵在屋内小声答应,可左叫右叫就是不见他出来,而儿媳刘氏也是默无一声。邹翁心中更加纳闷,不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便和老伴来到窗下将窗纸悄悄捅破向里面窥视,不料一看之下这房中一幕着实将二人吓了一大跳,只见自己的儿子被一根棕绳五花大绑的捆缚在床足下,衣衫凌乱精神萎靡,而床上萝帐轻垂人影晃动,似乎还有两个人。
老两口见状心中大骇,难道是家中昨天半夜来了强盗自己却一无所知,于是急忙问儿子道:“是何人将你捆绑?”天贵一脸惊恐的答道:“昨晚刚进洞房插好门闩,忽然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从床下钻出,将我用绳子捆绑在此,然后和新媳妇在床上睡了一宿。”邹翁闻听心中更惊,急忙问道:“那你为何不大声呼救?”天贵战战兢兢道:“我不敢,那汉子说我要是敢喊叫便立即杀了我。”话音未落,只见床帐一掀,随即一男一女从床上翻身下了地。这男子身材健硕肤色黝黑,一脸狞恶之色,而女子正是昨日刚刚过门的新媳妇刘氏,此刻兀自身着新衣,只见她满面绯红头发散乱,连看也不看公婆一眼。
男子几步走至天贵面前,从怀中摸出一把尺余长的杀猪刀来架在他的颈上,面向邹氏夫妇恶声道:“实话告诉你们,我本和陈氏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料她的父母嫌弃我贫穷,居然将她许配给你家黄口小儿,这一口恶气实难咽下。昨日我趁人不备早早便藏了进来,若是不让我尽欢而去,我就马上杀了这小子。”邹翁一听惊骇万分,眼见自己的爱子被其挟持,稍有不慎便会有杀身之祸,这天贵可是他们的独苗,平日爱若掌上明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那老两口也不用活了。眼见老伴陈氏惊吓过度几欲昏厥,他急忙一边扶住老伴一边对那汉子乞求道:“你千万不要鲁莽,有事好商量,只要不伤害我儿天贵,什么条件老汉都可以答应。”汉子大笑道:“此事甚易。你们赶紧去做些美味酒食先从窗口送进来,若是不丰盛或者不可口,我仍会杀了你们的宝贝儿子。”邹翁听罢心中暗暗叫苦,急忙命人下厨依言做好饭菜,又温好一壶美酒一并端来,放在窗台上。
那汉子虽说人长的粗鲁可心倒很精细,他生怕邹家在酒食中下药,于是先用一根长绳拴在天贵腰间,然后一手持绳一手持刀,命天贵走到窗边将酒食端回几案上,再让他将每样饭菜都尝几口,又喝了杯酒,等了片刻看他无事这才和刘氏一起吃了起来,吃完又命天贵将碗碟饭盒送至窗边让人端走。邹翁见此情形也无可奈何,想要报官却怕这汉子狗急跳墙杀了天贵,一时计无所出唯有顿足叹息而已。此时邹家早有好事者将此事传了出去,左邻右舍听说有人劫持新郎均大感惊讶,于是都纷纷到邹家来察看究竟,不料进门一看果真如此,众人心中均诧异万分,一时间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可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一晃三日已过,这汉子白天呼五吆六一味索取美味佳肴,到了晚上就将门户紧闭搂着新娘刘氏逍遥快活,而天贵却被锁在床脚,不仅一日三餐只能吃二人的残羹剩汤,时不时还被辱骂恐吓,白日提心吊胆晚上噩梦连连,只短短三日便已形销骨立憔悴不堪,邹家老俩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偏偏是束手无策。此时有几个邻居便让他报官,邹翁觉得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犹豫再三便同意了,为了不惊动那黑汉子便让邻居代他悄悄报了官府。当时修武县的县令姓徐,进士出身,刚刚到此地赴任不久,屁股还未在公堂上坐热就遇见了这咄咄怪事,开始心中还不甚相信,等带着一众衙役风风火火的赶到了邹家,进门一看才知果真如此,一众人等不由得暗暗称奇。
邹翁见父母官驾到犹如见到救星一般,急忙请徐县令进堂屋中上座,随即又让老伴奉上香茗。徐县令坐在堂中思虑良久,连茶都忘了饮,可一连想了数个办法,都因为投鼠忌器而不得不作罢。邹翁在旁见他眉头皱起冥思苦想,一时也不敢出声打扰。过了片刻徐县令忽抬头问他道:“你这儿媳可有父母?”邹翁起身答道:“有。就在邻村,离此约有数里地之遥”徐县令又问道:“她父母可曾来过?”邹翁道:“因事起仓促,也不曾告知他们,他们也没有来过。”徐县令面有疑色道:“这倒奇了,这三天此事传得沸沸扬扬远近皆知,他们是娘家至亲岂能不知?这中间怕是有什么缘由。”邹翁这几天为此事焦头烂额,本没时间想这些,此时听徐县令一说,心中也觉得有些蹊跷。徐县令问清刘氏父母所在,当即便命两个差役去邻村将他们带来。
过了一个多时辰,只见两个差役带着一对老年夫妇来到邹家,邹翁一看正是刘氏的父母,只是两人皆垂头丧气面有愧色。原来这几日他们在家中早已听说自己的女儿出此丑事,心中不由羞愧交加,生怕别人议论,也不敢出门,更不敢到邹家来,怕丢不起这个人。这天夫妇二人正在家中为此抹泪,忽见两个衙役上门相请,这才知道此事官府已经知道了,于是才不得不随差役来到邹家,因此一见亲家便脸颊发烧无地自容。徐县令问得他们几句便知事情缘由,原来这黑面汉子名叫陈黑子,与刘家同居一村,陈黑子自幼父母双亡,吃百家饭长大,目不识丁身无长物,好在身强力壮有一把子蛮力,所以尚能给人打短工赖以糊口。
前些年秋收农忙之时刘家曾请他前来帮忙,每日在家中忙里忙外出出进进。不想时间长了这小子居然和刘家的女儿素芳眉来眼去勾搭成奸还做下了苟且之事,刘父发现之后暴跳如雷,当即便将陈黑子赶出门外,为了遮丑赶紧找来媒人,将素芳许给了邹家,只当邹家的儿子年幼不知人事,尚能将这丑事掩住,不料陈黑子心有不甘,居然在素芳出嫁之时铤而走险做下如此无法无天之事,实在是让他们又惊又骇羞惭难当。徐县令问话完毕便让刘氏夫妇去窗外呼叫自己的女儿出来,可是任凭夫妇俩在外如何大声呼叫,素芳在屋内就是一声不吭。徐县令见状大怒,对刘氏夫妇道:“有女如此,可谓不孝之极。此皆为你们教女无方才致有此恶果,理应重重惩罚才是。”说毕便命衙役用鞭子抽打刘父二十下,刘母也被左右开弓掌掴十下,将二人打得哀嚎连连口中求饶不已。
待得打完,徐县令接着又命二人隔窗呼叫女儿,可素芳依然是不理不睬。徐县令见状命衙役继续鞭打刘父五十,掌掴刘母二十,打完再让他们呼叫素芳,不料素芳仍是置若罔闻默无一言。徐县令怒发如狂,当即命令衙役接着打,打完再叫,如是者数次。可怜刘父被鞭打共计二百余下,刘母也被掌掴了一百下,两人一个双臀紫红鲜血淋漓,一个鼻青脸肿面目全非,双双跪在门口声嘶力竭的哀求女儿,可房内却始终寂然一片。徐县令见状也无可奈何,只好命衙役先将刘氏夫妇带到偏房中,自己坐在堂中另思他策。正在他为之愁眉不展之时,旁边有一幕僚忽上前对他道:“大人,在下有一策不知可不可行?”徐县令闻听神情为之一振,当即道:“快快讲来。”
幕僚道:“前几日我们刚刚抓获一个盗贼关在狱中,此人名叫罗七,善于打洞钻穴窃人财物,我们不妨让他趁夜深人静之时潜至墙下悄悄打一个洞钻进去,先神不知鬼不觉将邹公子救出,然后再破门而入将这对奸夫淫妇拿住,如此则可避免投鼠忌器之嫌,不知大人以为此计如何?”徐县令听罢大喜,拍手对幕僚道:“此计大妙,就依你言。你此刻就去府中将犯人提出,只说事成之后大大有赏。”幕僚应了一声便去狱中将犯人提出带回,徐县令一看此人身材瘦弱形容猥琐,心中不由有些怀疑,不知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只是眼前也无别的良策,唯有用此人一试。眼看二更已过天色漆黑,陈黑子和刘氏吃饱喝足也早已上床安歇,徐县令先将此事告知邹翁并让他放心,保证不会伤害到天贵,接着便让十数个衙役悄悄埋伏在门口。
此时罗七在窗外聆听良久,确定屋内三人皆已酣睡之后这才蹑手蹑脚的来到墙下,用一把小锄头悄悄挖了起来。这罗七虽是貌不惊人身手却是不凡,也不见他怎么费劲就悄无声息的挖出了一个洞来,大小恰好能容一人钻进。罗七手脚并用悄悄从洞中爬了进去,将捆缚天贵的绳子用小刀割断,先将天贵口捂住将他叫醒,再对他打手势让他悄悄跟自己爬出来。天贵猛然被人摇醒先是大惊,若不是口被捂住差点便惊叫出来,好在他天资聪颖,见到罗七手势便知这是救他之人,当即便轻手轻脚随罗七从洞中钻了出来,待一到外面便有衙役将他接到堂屋中。邹翁及老伴站在外面提心吊胆等了半响,唯恐有个闪失害了儿子性命,直到此时见天贵安然无恙的被救出,心中这一块大石方算落了地,两人一进堂屋便抱着天贵嘘寒问暖喋喋不休,心中欢喜实所难言。
便在此刻就见徐县令将手一挥,只听轰然一声房门已应声而倒,埋伏在门外的众衙役一拥而入闯了进去。而床上二人正在酣睡,忽听一声巨响,还未及反应过来便被一群人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衙役又从枕下搜出凶刀一把,连同二人一并连夜解回县衙。第二日一早,徐县令便击鼓升堂审理此案。此时一城百姓均已闻听此事,纷纷扶老携幼前来听审,从门口到大堂挤得是水泄不通。徐县令命衙役将奸夫淫妇带来,众人一看这陈黑子须发纷乱黑丑可憎,而刘素芳却是纤腰弓足肤如凝脂,两人在一起反差如此巨大,不由让众人啧啧称奇。徐县令先将陈素芳提上,拍着桌子对其怒斥道:“本官见得各色人等多了,却从未见过有如你一般无耻,如你一般不孝之人,简直是猪狗不如。”说毕便命衙役上前将其全身衣服除去,不着寸丝片缕,然后先掌掴一百,和当日其母所受一样,再鞭笞二百,和其父所受数目相同,最后判其通奸之罪,杖责四十,命其父母领回,将邹家所下聘礼原数退还,让天贵另娶良家之女。
素芳默无一言脱衣受刑,转眼便双颊红肿皮破血流,待受刑完毕,刘家夫妇扶着女儿出了公堂,各自脱下自己的衣裤为女儿遮羞。而旁边围观的民众达数千人之多,纷纷上前将衣服又夺走,让刘素芳赤身裸体回了家。接着徐县令又命人带上陈黑子,判了个通奸挟持,意图谋杀的罪名, 用鞭子笞打两千下。这陈黑子身体甚为强健,寻常之人被鞭两千一般都抵受不住早早毙命,他却能得以不死,挨到第二日又被鞭笞了两千下,这次尚未鞭完即气绝而亡了。刘家夫妇自带着女儿回家后又羞又气,不到数年便先后病亡,而素芳没了依靠,又无人愿娶,最后居然投身勾栏做了烟花妓女,每有客人询问当年之事她便会娓娓道来,客人听得高兴往往会多给几个赏钱,她也能藉此糊口,而脸上因为被掴的伤痕一直都在,到老都未能消退。